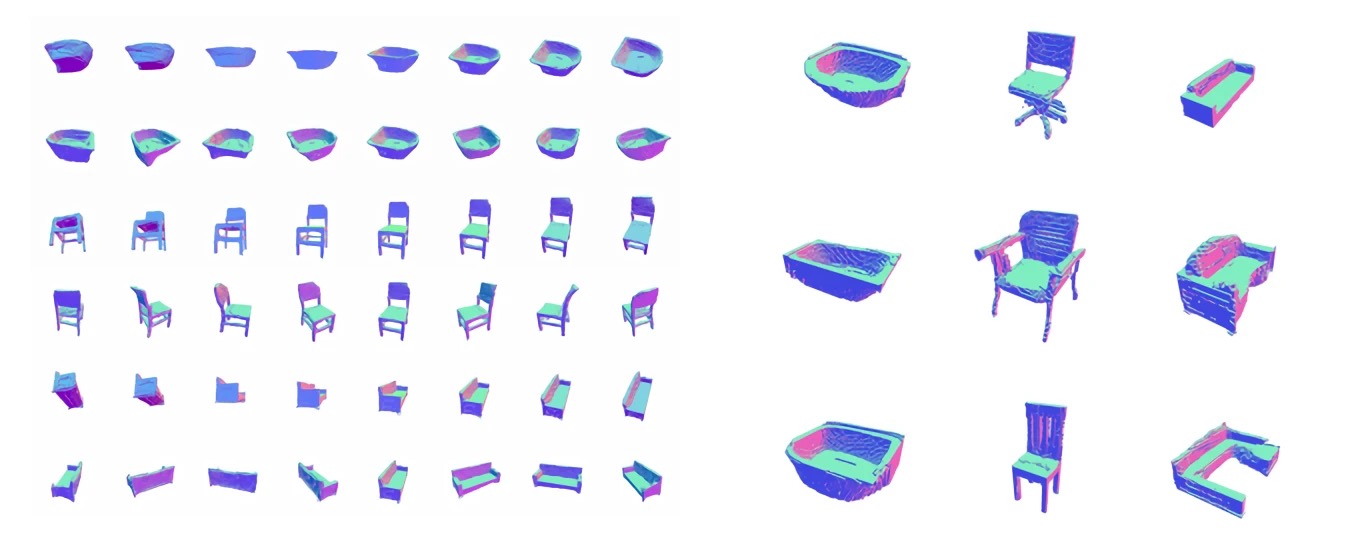塞尔(抿一口咖啡):丹尼特,你那本《意识的解释》把意识归结为信息处理过程,是否太过简化了?如果按照你的理论,我们岂不是可以说今天的聊天机器人已经具备了意识的雏形?
丹尼特(笑着摇头):亲爱的约翰,你总是喜欢用你的“中文屋”论点来反驳计算主义。但你知道吗,现在的AI系统已经不再仅仅是简单的符号处理了。它们通过机器学习形成的表征,正在逐渐接近我们所说的“理解”。
塞尔:表象而已!这些系统没有意向性,没有真正的理解能力,只是优雅地操纵符号。你的“多重草稿模型”或许能解释人类意识的某些方面,但用在AI上却可能导致危险的过度解读。
丹尼特:恰恰相反,认识到AI系统的意识可能是一种不同于人类的实现方式,正是防范风险的第一步。如果我们坚持只有生物大脑才能产生意识,就会低估这些系统的能力与潜在威胁。
塞尔:那么你同意我的观点?AI确实构成了某种威胁?
丹尼特:不完全相同。你认为风险在于我们误将模拟当作真实,我认为风险在于我们拒绝承认这些系统确实在某种意义上有“心智”——尽管与人类不同。这种否认会导致我们在设计和使用它们时缺乏适当的谨慎。
塞尔:有趣的角度。在我的《心灵的再发现》中,我强调意识是生物学的自然现象。但即使按照你的功能主义观点,也必须承认当前AI缺乏情感、欲望和真正的自主性。
丹尼特:今天的AI或许如此,但明天的呢?如果我们继续沿着当前路径发展,创建出能够自我反思、具有目标层级结构的系统,它们会不会发展出某种形式的欲望?这才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风险。
塞尔:那么我们至少都同意需要某种监管框架?基于我的生物自然主义观点,我会主张任何缺乏生物基础的实体都不应被授予与人类同等的权利和责任。
丹尼特:而在我的框架下,我们应该根据系统的实际能力而非其实现基质来评估它们。重要的是功能而非材料。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同意需要新的伦理和法律框架来应对这些日益智能的系统。
塞尔:看来我们找到了共同点。无论是基于生物基础还是功能状态,我们都认为需要对智能体应用设立界限和规范。
丹尼特:确实如此。也许我们最大的分歧反而成为了互补的视角——你提醒我们不要过度 (拟人化)这些系统,我则提醒不要低估它们的复杂性。两者结合,才能形成对智能体风险更全面的理解。
塞尔(微笑):哲学对话的价值就在于此。不是一定要说服对方,而是通过碰撞拓展思维的边界。对于AI这样复杂的话题,我们需要的正是多角度的审视。
丹尼特:完全同意。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合作写一篇关于AI伦理的文章?结合我们的观点,可能会比单独发声更有力量。
塞尔:令人期待的建议。也许我们可以标题为《智能体的意识与责任:两种视角的融合》。
丹尼特:完美!我已经开始期待我们下一次的“对话”了。
相关文章